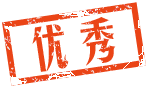有一种死法我们很熟悉
作者:湘里妹子
上午在办公室,同事看着《羊城晚报》说你们暨大饶芃子的博士生跳楼了。报纸上没有刊登照片,我不经意走过去一看,“余虹”两个字很赫然。我说原来是他啊。是个男的么?嗯。
很惊讶自己对死如此木然,更诧异自己怎么会对一个曾经“认识的人”的离去如此不在意。自己还没蜕变成异类吧?
我们若无其事般地马上又谈起了今年一月海珠区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欧阳女士的向活人的世界告别的同样方法。欧阳先生从5楼阳台纵身跳下,余虹先生从10楼高空坠亡。我想,虽然楼层的高低不同,但他们俩临跳前的勇气大概是一样的吧。
余虹是我在暨大读博时同在一个研究生楼进进出出时见到过的“熟人”,欧阳是我们湖南长沙人。
我完全能记起当年“认识”余虹的情景。1996年我在暨大读博的时候余虹在学校就小有名气了,主要是人们对他的个人生活谈得沸沸扬扬的。我的“同房”妇产科博士对研究生楼发生的各种事件很是熟悉,对研究生楼里传来传去的小道消息也颇感兴趣,她说据传你们中文系饶芃子的一个博士生余虹很有才气,一年半的时间就提前完成了博士论文(选择攻读文学比选择语言学容易一些的想法我就是听了这条“新闻”后产生的),关键是听说他还很重情义,听到他已经离婚的老婆割腕自杀,他还特意赶回四川在抢救过来的老婆床前伺候了半个月。哦,他老婆割腕不是为了他么?就算是为了他但是他们已经合法离婚了阿,你看多么有情有义。哦。据说不少女孩子自动送上门来要喜欢他呢。是么?我也要追追他试试,哈哈哈!啊?估计我当时张开的嘴很久难以合拢,因为“同房”的一串哈哈弄得我不知道她说的是真还是假。下次我见到他指给你认识认识。好。
有一次在暨大研究生楼门口我的“同房”突然兴奋地扯着我说,快看快看,那就是余虹。个头儿矮矮的,还很秃头,但有点儿与众不的魏晋风度。这就是余虹给我的第一印象。后来,“同房”多次追问我,非得让我说出余虹的哪点气质“与众不同”,我一时不知道如何来跟一个医学博士讲清楚魏晋风度。
余虹的这种死法倒是没有“与众不同”,而是赶上了与名人张国荣同样的时髦。
对于余虹的离去有人从“背景”的角度总结性概述了《令人扼腕的文人自杀》: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EmileDurkheim)在其《论自杀》中,将自杀的类型分为三种,即利己型,这种类型自杀的根源在于个人没有同社会融为一体;第二种为利他型自杀,即自杀者出于高尚的信念如宗教等;第三种为动乱型自杀,它的产生是由于个人缺乏社会约束的调节,个人需求和欲望的实现受到了社会的制约。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知识分子自杀事例最知名的是王国维的沉湖,其后的“文革”动乱中,出现不少知识分子集中性自杀的现象,比较著名的有翦伯赞夫妇、傅雷夫妇、老舍、邓拓……这些自杀多属于杜尔凯姆所说的第三种自杀现象。
一些研究者认为,民国以后,特别是“五四”以后,西方哲学、文艺思潮进入中国。我国的文化心理开始有所变化。西方的尼采、叔本华哲学、维护人的尊严的思想是促使他们走向自杀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伏清白以死直兮,故前圣之所愿”,“文革”时期一批知识分子的自杀,一方面是对极左路线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另一方面,“士可杀不可辱”的儒家文化心理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余虹的自杀究竟属于哪一种呢?比卧轨的青年诗人海子好像更复杂一点点吧?
有人这样说:“从这篇博客中也证实了余虹的选择或许并非遭遇了外界的不公,在一些人看来,或许,余虹对终极救赎的探究,让他陷入了一种对死亡的向往之中———在相当长时间内,余虹极有可能处于一种抑郁状态。”“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这是余虹今年9月在一篇博客文章的感言。
他自己亲手经营的个人生活有一点点糟糕,一直搅得他不得安宁,他希望寻找一种心灵的宁静。我就这么俗不可耐地“哥德巴赫猜想”着。
余虹刚刚把他儿子送往美国漂泊,老天,失去了父亲的儿子在异国能支撑下去的钱够不够哦?
学生在老师离去后,还在他的博客中留言诉说,死在这时被赋予了太多的哲学意味,他的举动成为生前最后一课。一位学生在他的博客这样留言道:“但我觉得这绝不是一个形而上学所思之‘终点’?毋宁说,更像一个您常常提及的‘原点’,一个海德格尔式的寓始于终的‘圆圈’。
其实,文人也好,粗人也罢,自己将生命毁灭的意义都是差不多的。画的是圆圈还是其他,只有他们自己最明白。
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双亲给的,生命是个过程,我们即便是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抑郁,也不能随随便便就终止这个过程阿。 2007-12-07 foshan nan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