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迪亚诺在中国最著名的崇拜者当属已逝作家王小波莫属。在小说《万寿寺》中,王小波对莫迪亚诺不仅仅作了引用——小说的开头直接以莫迪亚诺小说《暗灯街》的开头“我的过去,一片朦胧”作为开头,而是还直接借用了其作品的主题及结构。而另一外文学大碗王朔在自述《我看王朔》中甚至说:《玩的就是心跳》就是源自法国作家莫迪亚诺的《暗店街》,只是他学了个皮毛,只学会了把水搅浑,却无能力再次澄清,因而到后来不能自圆其说。
我的过去,一片朦胧——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条暗店街

作者:[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译者:薛立华 出版: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1986年 【作品简介】 《暗店街》的叙述者是位患了遗忘症的私家侦探。为了找到自己的真实身份,了解自己前半生的经历,他孜孜不倦地寻访可能是自己的那个人及其亲朋友好友的踪迹,他们出生或生活过的地点,他甚至远涉重洋,来到法属波利尼西亚的一个小岛寻找青年时代的友人。他的调查对象中有俄国流亡者、无国籍的难民、餐馆或酒吧间的老板、夜总会的钢琴演奏员、美食专栏编辑、古城堡的园丁、摄影师、赛马骑师等等。这些调查把读者带回到作者经常描述的被德军占领的年代。再现了这一黑暗时期法国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 【精彩书摘】 我的过去,一片朦胧…… 那天晚上,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我只不过是一个模糊的影子而已。当时,我正在等着雨停。那场雨很大,它从我同于特分手的那个时候起,就倾泻下来了。 几个小时前,我和于特在事务所里见了最后一次面,那时,他虽象以往一样在笨重的写字台后面坐着,不过穿着大衣。因此,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将要离去了。我坐在他的对面,坐在通常给顾客预备的皮扶手椅里。房间里,乳白色的玻璃灯具射出一道道强烈的光线照得我两眼发花。 “完了,居伊……一切部结束了……”于特说罢,长叹了一口气。 写字台上,摊着一卷档案材料。它也许是那个身材矮小、头发棕褐、目光惊愕、脸部浮肿的男人的,他委托我们跟踪他的妻子。那天下午,她要去和另一个身材矮小、头发棕褐、脸部浮肿的男人幽会,地点是在同保罗-杜梅林荫大道相邻近的一条街上,即维塔尔路上一家备有家具的公寓里。 于特沉思地捂着胡子。那灰白色的短胡子,把他的两个腮帮子都盖满了。他那一对通常很亮的大眼睛,此刻显得茫然失神。在写字台的左边,放着我在工作时坐的柳条椅子。在于特的背后,一些深色的木制书架挡住了半壁墙。书架上面,放着最近五十年来的各种《博坦》(一种电话簿)和年鉴。以前我常听于特说,这些工具书是他须臾也不能离开的,任何别的东西都无法代替它们。他还说,这些《博坦》和年鉴是人们所能拥有的最珍贵、最生动的图书馆,——因为在它们的一页一页上,汇编着许多人和事以及一些现已不复存在的行当(比如掏烟囱、杀猪等),它们只有在这些《博坦》和年鉴上才能查到。 “这些《博坦》,您打算如何处理呢?”我问于特,同时抬手指了指书架。 “居伊,我把它们都留在这里。这套房子,我将继续租下去。” 他迅速地扫视了一下周围。通向隔壁小间的两扇门敞开着,可以瞥见里面旧的天鹅绒长沙发、壁炉以及反映出一排排《博坦》、年鉴和于特的面孔的一面镜子。在这个小间里,经常等候着我们的顾客。地板上,铺着波斯地。墙上靠近窗子的地方,挂着一幅东正教的圣像。 “居伊,您在想什么?” “什么也没有想……那么说,您要继续付租金了?” “是的。我不时还要回巴黎来,事务所就是我的落脚点。” 他把香烟盒向我递来。 “只有使事务所保持原来的样子,我的心里才能好受一些。” 我们在一起工作,已经八年多了。一九四七年,他亲手创建了这个私家侦探事务所。在我来到这里以前,他已和其他好多人共过事了。我们的职责是向顾客们提供一些于特称之为“风化情报”的东西。“这一切都发生在,”于特常常得意地这样说,“‘上流社会的人们’中间。” “您觉得您能住到尼斯去吗?” “当然可以。” “您不会感到腻味吗?” 他喷出一口烟雾。 “居伊,人总有一天要退休的。” 于特笨重地站起来。他的体重大概要超过一百公斤,身高可能有一米九五。 “我乘晚上八点五十五分的火车走。还有点时间,我们还来得及喝上一杯呢。” 他走在我前面,我们一起来到了通向前厅的走廊。前厅的形状稀奇古怪,是椭圆形的,墙壁上的颜色呈浅灰褐色,有些地方已经褪色了。地上,扔着一只黑色的公文皮包,因为里面的东西塞得太鼓,它的盖子已经无法关上了。于特把它捡了起来,用手托着拿走了。 “您没有什么行李吗?” “我把一切都预先托运走了。” 于特打开大门,我关上了前厅里的灯。在楼梯的平台上,于特踌躇了一会,然后才把大门关上。关门的金属碰撞声使我感到揪心,它标志着我一生中的一段很长的时期结束了。 “哎,居伊,真叫人伤心啊,不是吗?”于特一边对我说,一边从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一块大手绢,擦着额头。 门上,仍然挂着那块长方形的、黑色的大理石板,上面刻着金色的、并以闪光片装饰起来的两行宇: C·M·于特 私家侦探 “我把它留在这里,”于特对我说。 接着,他把钥匙在锁眼里转了一圈。 我们顺着尼埃尔林荫大道,一直走到佩雷尔广场。虽然是在夜间,而且早已进入冬季,但是天气还很暖和。到了佩雷尔广场,我们坐在“绣球花”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于特喜欢这家咖啡馆,因为这里的椅子“和以前一样”,是细藤编花的。 “您呢,居伊,您以后怎么办呢?”他喝了口兑水的高级白兰地,这样问我。 “问我吗?我正在追踪一条线索。” “一条线索?” “是的,关于我过去的一条线索……。” 我用夸张的语气说出这句话,弄得他笑了。 “我总是相信,有一天您一定会找到自己的过去的。” 这一回,他态度严肃,我很受感动。 “但是您得考虑考虑,居伊,您这样做是否真的有必要,我可吃不准……” 他缄默不语了。他在想什么呢?在想他自己的过去吗? “我给您一把事务所的钥匙。您随时都可以到那里去。那样会使我高兴的。” 他递给我一把钥匙,我把它放进我的裤袋里。 “打电话到尼斯来找我。随时告诉我……有关您过去的事……” 他站了起来,同我握手。 “你要不要我送您上火车?” “啊!不!……不必了,……那太叫我伤心了……。” 他只一步就跨出了咖啡馆,头也没有回。我的心里,立即出现了一种空虚的感觉。对我来说,这个人一直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他,没有他的帮助,我真不知道自己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因为在十年前,我突然患了遗忘症,犹如堕入五里雾中。他同情我的处境,并且靠他的门路多,甚至还使我获得了户籍。 “拿着吧,”他那时一边对我说,一边递给我一只大信封,信封里装着一张身份证和一本护照。“现在,您叫‘居伊·罗朗’了。” 这个私家侦探,我以前曾经求他帮过忙,请他用他的机智协助我寻找我过去的证据和踪迹。此刻,他接着又说: “我亲爱的‘居伊·罗朗’,请您从观在起,不要再往后看了,多想想现在和将来吧。我建议您和我一道工作……” 如果说他同情我,那么这是因为他本人的记忆也有漏洞——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失去了他自己的踪迹,他一生中的整整一个时期一下子变得模糊不清了,没有留下一点线索,没有留下一丝一缕还能同过上挂上勾的关系。可不是吗,我目送着在夜色中离去的这个身着旧外套、挟着黑色大公文皮包、年迈力衰的男子,他同过去那个波罗的海的网球好手、长着金黄色头发的英俊男爵康斯坦丁·冯·于特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摘自《暗店街》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著/薛立华 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
作品简介:《青春咖啡馆》是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最令人心碎的作品之一。作品中一如既往地充满了调查与跟踪,回忆与求证,找不到答案的疑问。 在巴黎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靠近卢森堡公园的奥黛翁,有一家名叫孔岱的咖啡馆。它像一块巨型磁铁一样,吸引着一群十八到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他们“四处漂泊,居无定所,放荡不羁”,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从不考虑未来,享受着文学和艺术的庇护。 《青春咖啡馆》是莫迪亚诺创作的第二十五部作品,二〇〇七年出版后两周销量即突破十万册,并被法国《读书》杂志评为“二〇〇七年度最佳图书”。而在201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由金龙格翻译的《青春咖啡馆》获得傅雷翻译出版奖。 青春咖啡馆——莫迪亚诺最令人心碎的作品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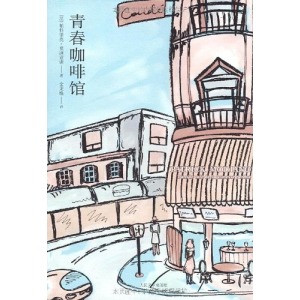
书名:青春咖啡馆 作者:[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著译者:金龙格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05月 【精彩书摘】 那家咖啡馆有两道门,她总是从最窄的那扇门进出,那扇门人称黑暗之门。咖啡厅很小,她总是在小厅最里端的同一张桌子旁落座。初来乍到的那段时光,她从不跟任何人搭讪,日子一长,她认识了孔岱咖啡馆里的那些常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跟我们年纪相仿,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在十九到二十五岁之问。有时候,她会坐到他们中间去,但大部分时间里,她还是喜欢坐她自己的那个专座,也就是说坐最里端的那个位子。 她来咖啡馆的时间也不固定。有时,你会发现,她早晨一大早就坐在那里了。要么,到午夜时分,她才出现,然后在那里一直待到咖啡馆打烊。在这个街区,这家咖啡馆还有布盖和拉贝格拉是关门最晚的,但孔岱却云集了最千奇百怪的顾客。岁月流逝,我常常不由自主地问自己,是否仅仅因了她的存在,才使得那家咖啡馆和那里的人都显得那么异乎寻常和与众不同,仿佛她用自己的芬芳把他们都浸透了。 我们来做个假设,假设有人用一块布条蒙住你的眼睛,把你带到那里,让你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下,然后揭掉蒙眼布,给你几分钟时间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现在是在巴黎的哪一个街区?这时候,你可能只要观察一下周围的邻座,听一听他们的谈话内容,随即便能猜出:是在奥黛翁交叉路口的附近地区,在我的想象中,这个地区下雨天总是灰蒙蒙的一片。 有一天,一名摄影师走进了孔岱。从外表上看,他跟店里的顾客没有任何分别。同样的年龄,同样的不修边幅。他穿着一件对他来说太长的上衣,一条平纹布裤子和一双肥大的军用皮靴。他拍摄了大量经常光顾孔岱的那些客人的照片,然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常客,如此一来,在其他人看来,他拍的好像是全家福。后来,这些照片登在一本以巴黎为主题的摄影画册里出版,照片下面的说明义字很简单,只列有这些顾客的名字或者外号。她在好几幅照片中都出现过。就像电影中常说的那样,她比其他人都上镜。在照片上的所有的人当中,读者最先注意的是她。在摄影厕册页脚的说明文字中,她的名字是“露姬”。“从左到右分别是:扎夏里亚,露姬,塔尔赞,让一米歇尔,弗雷德和阿里·谢里夫………”“近景,坐在吧台边的是:露姬。在她身后是:安妮特,堂·卡洛斯,米海依,阿达莫夫和瓦拉医生。”她站得直挺挺的,但其他人的姿势却很随意,比方说,那个名叫弗雷德的人甚至把头靠在那张仿皮漆布长椅上呼呼睡着了,很显然,他已经好几天没刮胡子。有一点必须明确:露姬的名字是在她开始频繁光顾孔岱的时候,别人给起的。有一天晚上,临近午夜时分,她走了进来,当时我也在场,店里只剩下塔尔赞、弗雷德、扎夏里亚和米海依,他们都世在同一张桌子边。塔尔赞大叫起来:“哎呀,露姬来了……”起初,她显得有些惶恐,但没过多久她的脸上便绽出了微笑。扎夏里亚站了起来,装出一副很庄严的口气说道:“今天晚上,我为你命名。从今往后,你名叫露姬。”久而久之,他们当中所有的人都叫她露姬,我现在想来,她有了这个新的名字之后,反倒觉得放松了。是的,是放松了。实际上,我越往深里想,越能找到我最初的印象:她到孔岱这里,足来避难的,仿佛她想躲避什么东西,想从一个危险中逃脱。见她坐在最里头,坐在那个谁也不会注意到她的位置时,我就有了这种想法。当她混杂在其他人中间时,并不引人注目。她总是一言不发,谨小慎微,甘当他们的听众。我甚至觉得,为了更加安全起见,她喜欢呆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宁愿和那些“大嘴巴”混在一起,否则的话,她不可能几乎总是坐在扎夏里亚、让一米歇尔、弗雷德、塔尔赞和拉欧巴那一桌……和他们在一起,她便融人到整个布景当中,只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无名的哑角,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物,在照片的说明文字会这么标注:“名字不详”,或者简明扼要地写上“某某”两个字。是的,她刚开始在孔岱出现的时候,我从未见过她与什么人有亲密的关系。从那以后,其中的一个大嘴巴在后台叫她露姬便没有任何妨碍,因为这不是她的真实名字。 不过,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她在一些细节方面跟其他人截然不同。她的衣着非常讲究,跟孔岱的其他客人形成鲜明的反差。一天晚上,她坐在塔尔赞、阿里·谢里夫和拉欧巴的那张桌子,点了一支娴,她那修长的手指让我心头为之一震。尤其让我吃惊的是,她的指甲熠熠闪亮。指甲上涂着无色指甲油,这个细节也许显得微不足道。那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为此,我们必须具体介绍一下孔岱里的常客。他们那时的年龄在十九到二十五岁之间,只有个别的客人,像芭比雷、阿达莫夫和瓦拉医生差不多五十岁了,但是大家忘记了他们的年龄。芭比雷、阿达莫夫和瓦拉医生都忠贞不贰地坚守着自己的青春,坚守着人们或许称之为“浪子”的这个陈旧过时但悦耳动听的雅号。我在词典里查阅“浪子”的含义:指四处漂泊、居无定所、放荡不羁、无忧无虑的人。这个释义倒是很适合这些经常出入孔岱的男女。他们中的一些人,譬如塔尔赞、让一米歇尔和弗雷德,都声称自己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屡屡和警察打交道,而拉欧巴十六岁的时候就从善心巴斯德少年犯教养所里逃了出来。但是,大家都在左岸,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在文学和艺术的庇护之下。我呢,我在那里上学。我不敢把我上学的事情告诉他们,我并没有正儿八经地融入到他们的那个圈子里面。 (节选自《青春咖啡馆》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北京时间10月9日19点,瑞典学院宣布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其代表作有《暗店街》《八月的星期天》等。虽然不是此前预测的大热门,莫迪亚诺的获奖也并不算爆冷。不少业界人士也认为他早就该获诺奖。他的好几部作品早就被引进中国,并影响了不少作家。王小波和王朔都是他的粉丝,并曾经在各自的小说中以不同的方式向他“致敬”。 
莫迪亚诺的中国粉丝,名字叫王朔和王小波
◎吴永熹
《暗店街》有四个译本
与去年的诺奖得主爱丽丝·门罗不同,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在中国是一个熟悉的名字。他的名作《暗店街》于1984年就被译成中文出版,而最受中国读者追捧的王小波则公开在作品中向他“致敬”。他是一个让我们倍感亲切的作家——到现在为止,《暗店街》在30年间已经有了四个译本。1984年《外国文艺》杂志上署名“小禾”的译本,198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薛立华译本,1992年漓江出版社的李玉民译本,最近的是1994年译林出版社的王文融译本。 衡量一个作家的地位,译本的多寡是标准之一,莫迪亚诺在30年间被反映出版了十来种著作,《暗店街》更是有了四种译本之多,或许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读者对他的热情。与此相应的,是两位中国流行作家,王朔和王小波都曾经公开表达莫迪亚诺对自己的影响。王朔在自述《我看王朔》中甚至说:《玩的就是心跳》就是源自法国作家莫迪亚诺的《暗店街》,只是他学了个皮毛,只学会了把水搅浑,却无能力再次澄清,因而到后来不能自圆其说。到底王朔怎样只学了个皮毛,怎样地“把水搅浑,却无能力再次澄清”?王朔谦虚的夫子自道,倒是给读者与评论者提出了一个值得仔细思考的问题。 1978年出版的《暗店街》是莫迪亚诺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获得了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奖。书中的主人公在偷越边境时遭遇劫难,受到刺激后丧失了记忆。主人公开始用探案技术在茫茫人海中调查自己的身世和来历。这部作品揭示了莫迪亚诺作品的重要主题:记忆、过去、身份。主人公搜集了大量片断,试图拼凑出自己的人生。而加入侦探小说的元素也是莫迪亚诺作品的一大特色。 王小波受其影响 随着《暗店街》的成功,1987年,世界知识出版社推出了莫迪亚诺的《青春狂想曲》。在这部作品中,莫迪亚诺再一次发掘了记忆的主题,他让年近中年、生活安乐的主人公回到他二十年岁的人生经历,回到占领时期的巴黎,召回阴郁悲哀的青春时光。1993年,漓江出版社推出《一度青春》一书,其中收录了《一度青春》(即《青春狂想曲》)、《往事如烟》和《凄凉别墅》三部小说。 1992年,花城出版社推出莫迪亚诺的《八月的周日·缓刑》一书,书中收录两个中篇,《八月的周日》及《缓刑》。 90年代早期以后,对莫迪亚诺作品的译介有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沉寂,直到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他2003年的新作《夜半撞车》。因为这部小说,莫迪亚诺在中国获得了一项文学奖——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在这本书里,记忆依然有着幽灵一般的朦胧的品质。 莫迪亚诺近年被译介的作品,主要有《青春咖啡馆》、《地平线》等。 莫迪亚诺在中国最著名的崇拜者当属王小波莫属。在小说《万寿寺》中,王小波对莫迪亚诺不仅仅作了引用,而是直接借用了其作品的主题及结构。显然,就像莫迪亚诺一样,王小波也是一个对记忆有着深刻兴趣的作家,他的大量作品都是从一个较晚近的时点,追忆自己青春时代的故事,并将我们带往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文化革命”与知青下乡。而阅读莫迪亚诺的作品无疑给中国作家王小波带来了新的启发——他让王小波发现,通过一种略带神秘与寓言色彩的设定,记忆将会给文学带来无尽的可能性。和《暗店街》的主人公一样,《万寿寺》的主人公也失去了记忆,而作为一个失忆之人,他接下来的行为动机便是去寻找自己的过去。《万寿寺》中“我”的神秘失忆,与莫迪亚诺作品中大量解释不充分的、颇具神秘色彩的失忆有着相同的性质,它将主人公抛入一团迷雾之中,陷入一种极大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让主人公进入了一种全新的、对存在加以探询的空间。 王小波写道:“在我眼前的,既可以是这层白内障似的、磨砂灯泡似的空气,也可以是黑色透明的、像鬼火一样流动着的空气。人可以迈开腿走路,也可以乘风而去。”正是在莫迪亚诺的启发之下,王小波在他的作品中进行更为自由和天马行空的探索——在一个不稳定的、寓言的世界里,一切都是可能的。由此,我们也收获了中国当代文学中最为丰美与奇诡的一批作品。 |